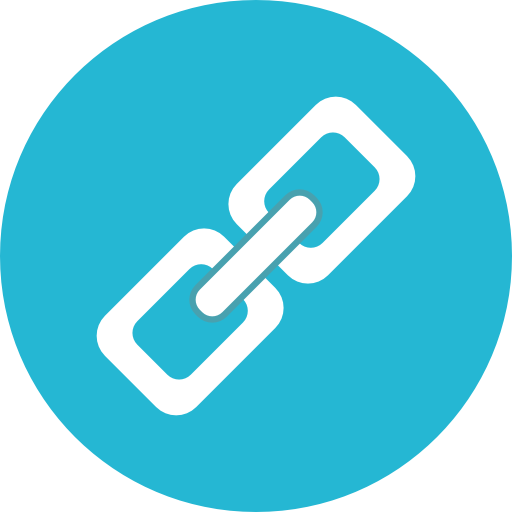作者:王梓晨 2025年8月23日
8月中旬,中国企业家转互联网名人罗永浩在多个中国平台上推出了长视频播客节目《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节目以深度对话为主;他的首位嘉宾是新兴电动汽车品牌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节目时长长达五小时,这种形式立即爆火,在单一平台上几乎瞬间就达到了超过两百万的观看量——这证明了中国重量级创作者开始效仿Lex Fridman和Dwarkesh Patel。
几乎同时,《金融时报》的Edward White报道称,中国的播客听众数量可能在2025年达到约1.5亿,比五年前不到一百万大幅增长——这一激增是由创作者在日益增长的好奇心和监管边界之间导航推动的。
尽管名人推出播客节目且听众数量激增,但中国独立播客主播仍在苦苦挣扎。原因在于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差异:在美国,创作者拥有自己的受众并通过信任变现;在中国,创作者的自主权受到平台控制、交易式变现以及受限的注意力环境的限制——尽管微妙,但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在美国,播客是基于RSS构建的——一种开放、去中心化的订阅源,让创作者广泛分发音频。一旦发布,创作者就拥有了关系。如果他们切换平台,听众会跟随。苹果、Spotify等平台充当发现工具,而不是守门人。创作者可以通过Patreon、订阅、赞助、主播朗读广告、现场活动、周边商品和捐赠等方式可持续变现——无需平台批准。即使视频播客爆炸式增长,开放的分发模式也保持不变:美国听众越来越多地在YouTube上消费播客,这说明视频增加了新的触达范围,而没有封闭分发。
这种开放系统构成了基于信任的变现基础,这种基础特别坚韧。Nielsen发现,主播朗读广告——自然嵌入到节目中的广告——比制作广告产生更高的品牌回忆和转化率,因为它们利用了听众对主播声音的信任。美国播客广告收入在2023年达到19亿美元,并预计在2024年超过20亿美元,创作者通过关系和社区直接赚钱——而不仅仅是交易式内容销售。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文化和生活方式因素放大了美国播客的优势。许多美国人住在郊区,开自己的车上班——通常在私人空间中花费30-60分钟通勤。即使在大流行后,2022年仍有68.7%的美国工作者独自开车通勤。这创造了长时间的空闲时间,眼部被占用但耳朵空闲——非常适合60-90分钟的深度播客。此外,许多美国家庭有私人办公室或安静角落,更大的个人空间支持在更舒适的环境中进行长时间聆听。
转向中国,创作者在平台主导的、精选生态系统中运作。像喜马拉雅、荔枝、蜻蜓和小宇宙这样的平台集中策划、推荐、变现甚至审核内容。创作者上传内容,但发现、可见度和受众连接仍受平台约束。与美国不同,如果平台算法变化,创作者无法轻易将听众转移到其他地方。平台推动算法友好的格式——付费知识课程、有声书、情感脱口秀——挤占了依赖缓慢建立听众忠诚度的利基、音频优先播客。
以喜马拉雅为例:2023年,它实现了61.6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和2.24亿元人民币的净利润,展示了可扩展性——但主要是平台的业务。腾讯音乐斥资数十亿收购喜马拉雅,进一步巩固了对可变现金音频内容的控制。
中国播客变现仍主要以交易为主。用户购买内容,而不是社区。一旦支付完成,关系就结束了。当更便宜或更快的资讯出现在抖音、Bilibili或短视频平台上时,参与度会急剧下降。主播朗读广告模式难以确立,因为品牌——面对不明确的品牌安全规范——更喜欢标准化、制作广告,而创作者缺乏对信息和放置的控制。因此,很少有独立音频优先创作者能够维持全职职业;许多人依赖跨平台收入——从微信群到咨询和直播电商——来生存。
注意力环境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播客。2024年,中国城市地铁出行达322.4亿人次。地铁拥挤、嘈杂且注意力碎片化——不适合沉浸式聆听。相反,快速、高度刺激的媒体获胜。像抖音(TikTok的中国姊妹版)和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在微互动中蓬勃发展。
此外,中国短视频平台已经达到了成熟度和文化渗透水平,使它们在结构上具有竞争优势。抖音、快手以及在一定程度上Bilibili,不仅主导用户时间,还主导内容格式、推荐算法和变现基础设施。它们的算法高度个性化,并优化为在几秒钟内提供多巴胺触发体验,使它们深深嵌入日常生活中——从早间地铁出行到睡前刷屏。对于许多中国用户来说,打开抖音或快手已成为默认行为,经过多年的习惯强化和网络效应培养。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播客听众数量增长,创作者也面临严峻挑战,与高度设计的短视频生态系统争夺时间和心理空间,而这些系统已经“赢得”了注意力经济。
尽管有这些障碍,中国的播客听众仍在增长——从不到一百万到2025年预计的1.5亿——尽管仍未达到短视频的规模。
另一个微妙因素是审查制度。虽然不像正式禁令那样严格,但创作者往往自我审核内容——避免敏感话题或故意挑衅——以维持平台可见度。这种限制阻碍了美国有影响力的播客所特有的那种真实、探究性的对话,在那里创作者可以更直率地讨论政治、文化或社会批判。结果:中国的播客往往保持信息性或情感安全,限制了受众参与度和社区忠诚度的深度。
当然,他们不断在推动界限。两个月前,《怪异说》的谢若含和王磬与北京大学的赵宏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陈碧副教授讨论了各地公安部门对数十名网络男同性恋色情小说作家的迫害。
那么,为什么像罗永浩这样的人能推出成功的视频播客,而独立音频优先主播却在挣扎?因为像Bilibili这样的视频生态系统已经提供了可发现性、变现功能、审核基础设施和受众聚合。罗永浩的名气加上平台的动力等于触达;没有平台或名人地位的独立音频主播必须对抗算法和注意力潮流——一场上坡战。
中国独立创作者能否复制美国模式?三个结构性转变将有所帮助。首先,受众可移植性——允许RSS或可互操作的订阅源,让创作者迁移并拥有他们的订阅者关系。小宇宙FM已经开始在这里进行探索性步骤。其次,建立可靠的主播朗读广告市场——有商定的品牌安全标准和测量能力——可以允许基于信任的变现。第三,开发会员和基于社区的支持模式——从交易式内容销售转向持久的创作者-听众关系——将加强可持续性。
在这些条件演变之前,中国的播客将在数量上增长但仍脆弱。受众扩张值得注意——但创作者的经济可行性仍受平台、注意力限制和监管舒适区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