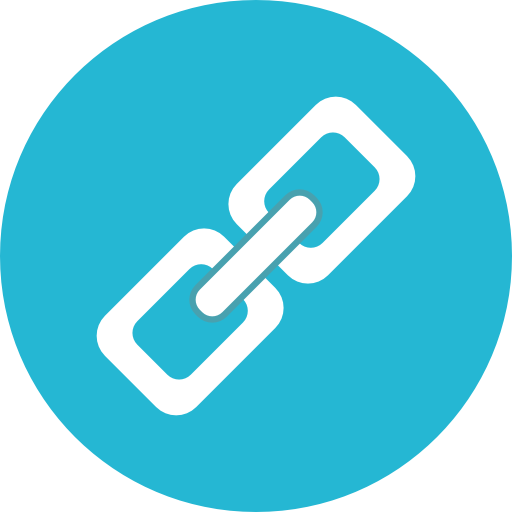如果只看标签,但斌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里最“稳定”的那一类人:价值投资者、长期主义者、巴菲特拥趸、重仓龙头、不爱折腾。可如果顺着他最近几年的持仓、访谈和公开表态一路看下来,又会产生一种微妙的错位感——这个看起来最传统的价值派,正在比很多“成长派”更激进地谈论AI。
问题于是变得有趣:这是一次风格突变,还是一次长期方法论的自然延伸?
更现实的答案是后者。
但斌从来没有把“价值投资”理解成对某些行业的终身信仰,而是把它理解为:持续寻找能够在长期创造巨大自由现金流、并且难以被替代的企业。行业可以换,技术可以换,时代叙事可以换,但这个筛选逻辑不能换。
如果站在这个框架下回看他二十多年的投资轨迹,会发现其实高度自洽。
在中国经济高速扩张阶段,最容易形成护城河的是消费品龙头,是白酒、家电、调味品,是能吃到城镇化、收入提升和品牌溢价红利的公司。那时押注消费,本质上是在押注中国社会结构的升级。
当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换挡,而全球科技周期重新成为决定资产回报的主线时,价值锚点自然开始迁移。
但斌并不是突然“爱上AI”,而是逐步得出一个结论:未来十年,决定企业长期价值的最重要变量,将从“卖什么产品”,转向“掌握多少算力、多少数据、多少平台入口”。
这是一种生产要素层面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的护城河来自渠道、品牌和规模,那么AI时代的护城河,更多来自算力资本开支能力、模型迭代速度、生态粘性以及平台级分发能力。
本质上,这是一次从“产品时代”走向“平台时代”的深化。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所谓“全面牛市”的预期一直非常克制。他更愿意用“结构性行情”来描述未来几年的市场状态。
经济并不会同时奖励所有行业。资本只会流向少数能够持续扩张边界的领域。
在他的框架里,真正值得长期下注的机会,通常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技术范式正在发生跃迁、行业集中度有持续提升空间、头部企业具备不断自我强化的能力。
AI几乎是少数能同时满足这三点的赛道。
很多人担心AI估值过高,而但斌的态度恰恰相反:如果一个技术浪潮真的有能力重塑生产率,那么最危险的事情,往往不是泡沫,而是过早离场。
历史上几乎所有改变世界的技术,在早期阶段都伴随着“看起来很贵”。
互联网是这样,智能手机是这样,云计算是这样。
真正决定长期回报的,从来不是买在最低估值,而是有没有持有到产业完成定型的那一天。
这也是他近两年组合变化的核心线索。
早期AI行情中,市场最容易定价的是硬件——GPU、代工厂、服务器产业链。但随着算力逐步进入规模化阶段,边际收益最高的环节开始向上游平台和应用层转移。
硬件更像基础设施,平台更像收费站。
因此可以看到,他在逐步降低对部分AI硬件外围资产的配置,同时提升对平台型科技公司的权重。
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这类公司,本质上不是单一业务公司,而是拥有多重现金流引擎的超级平台。一旦AI成为通用能力,它们可以在搜索、广告、云、办公、内容分发等多个场景中反复变现。
这类公司最大的优势,不在于“有没有某一款爆款模型”,而在于:即使模型迭代方向发生变化,它们也有足够的资源不断跟上。
换句话说,这是对“持续参与资格”的投资。
在地域配置上,他同样显得非常现实。
美股之所以成为其资产组合中的核心,并不是情绪偏好,而是因为全球最重要的科技公司,几乎全部集中在那里。
创新密度决定长期回报率。
在这个前提下,美股更像是全球科技资产的“主交易所”,而A股与港股更多承担的是补充和结构性机会的角色。
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本土市场,而是对周期位置的判断更加清醒:地产下行周期尚未完全出清,传统产业难以承担长期主线的角色,因此只能在少数具备技术突破可能的细分领域中寻找机会,例如创新药、机器人等。
组合结构上,他一直坚持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原则:大部分仓位放在“已经证明自己能赚钱的巨头”,小部分仓位用于押注“可能改变格局的新物种”。
这是一种用确定性去对冲不确定性的配置方式。
在风险管理层面,他的底线其实比外界想象得更保守。
例如,当产品净值低于某个阈值时主动暂停管理费;例如在极端波动中,更关注流动性和组合韧性,而不是追逐短期弹性。
这背后是一种很朴素的逻辑:只要活着,就永远有下一次机会。
真正毁掉投资者的,往往不是一次亏损,而是被迫出局。
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会发现一个重要结论:但斌并没有从“价值投资者”变成“科技投机者”。
他只是把价值锚点,从中国城镇化红利,迁移到了全球科技生产率红利。
方法论没变,时代变量变了。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最大的机会来自“让十几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未来十年,最大的机会可能来自“让AI和机器替人干更多的活”。
从这个角度看,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像是一场提前布局,而不是追逐风口。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反复强调:错过时代级别机会的风险,远大于短期回撤的风险。
当一个结构性浪潮真正展开时,最大的成本从来不是买贵一点,而是根本没有上车。
而这,或许才是“老派价值投资者”在新时代给出的最现实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