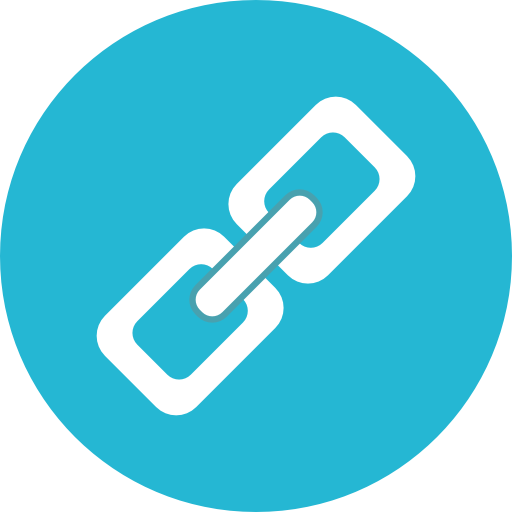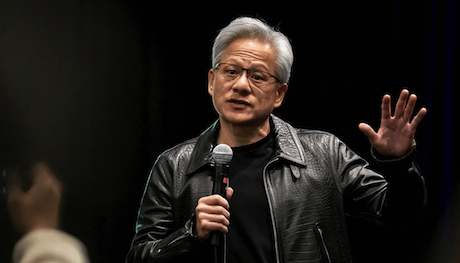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总给人一种“稳到不行”的错觉:身披皮衣,口袋里揣着算力时代的金钥匙,市值动不动上万亿。可他自己从来不这样看。他在那场长达两小时的访谈里坦承,过去三十多年,每天起床都觉得公司还剩三十天就要倒闭。这话听上去夸张,却一点都不矫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极端、甚至近乎偏执的现实主义,自带初创公司那种“随时暴毙”的危机感。
这份危机感不是装出来的。英伟达刚起步那几年几乎每一程都踩在悬崖边:1995 年方向赌错,差点资金链断裂;靠世嘉投的区区 500 万美元续命;靠台积电那一次非典型的信任过关。那不是“科技创业的浪漫”,那是纯粹的生存。如果你把今天的英伟达当成一个铁板一块的科技帝国,不妨回头想想这个细节——这家公司有好几次根本不该活着走到今天。
也因此,当人们问他怎么看待当前的人工智能竞赛时,他用的比喻很轻描淡写:这根本不是百米冲刺,看不到任何终点线;更像一场不断往前延展的越野,每个人都踩着上一个人的轨迹继续跑,没人有机会独占山顶。这个观点和市场上那些喜欢煽情的“奇点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热衷于描绘一种突然爆炸式的技术突破,好像某个清晨醒来你会发现世界被一种全新的智能重新格式化;而在黄仁勋眼里,AI 的进步虽然快,但不是那种魔术式的突变,而是持续、稳扎稳打、不断校准的迭代。
他讲了一个很实在的判断:过去十年算力提升了十万倍,可真正推动这十万倍的,不是让 AI 更放飞,而是让它学会更谨慎地思考。算力不是让 AI 变成一个更鲁莽的玩家,而是让它变成一个更严谨的学生。这个判断听上去很朴素,但对于一家几乎是算力供应商中的“地心引力级客体”的公司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方向宣言——AI 的基础设施不是用来放大风险,而是用来缩小误差。
英伟达真正赌大的那次,是 2005 年的 CUDA。那套编程架构推出后股价直接被腰斩,又被腰斩,总计跌了 80%。谁都看不懂它要干嘛,连英伟达内部也不是人人都相信。可黄仁勋坚持下来了,用了一种外行听了都会倒吸凉气的方式坚持:直接投产。芯片还没完全验证就送去流片。这种做法在芯片行业几乎算“赌命”。他解释说:因为他知道它能工作,所以要押重注。这种直觉式的“工程狂信”,在多数公司会被写进反面教材,但它在英伟达那里成了奠基的一步。现在人人都在谈“CUDA 生态”,仿佛它理应存在;可如果那一年流片失败,今天的英伟达大概率正在某个博物馆的“技术墓地”里安眠。
这也是黄仁勋谈竞争时最常提到的一点:所谓迭代,不是重复,而是从第一性原理不断反问: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下一步是否能再推远一点?他不相信一劳永逸的突破,只相信持续踩着正确方向的那种“固执的更新”。听上去有点像创业鸡汤,但从一个早期差点被时代抛下三次的人嘴里说出,就成了另一个意味:你不坚持迭代,世界会替你淘汰;你坚持了,也未必活下来,但至少不是死于自己的幻觉。
有趣的是,他在讨论工作和被 AI 取代的问题上,提出的不是技术逻辑,而是“目的论”。他说,判断你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替代,核心不是看 AI 能不能完成你的任务,而是问一句更残酷但更诚实的问题:任务是不是你工作的全部目的?他举了放射科的例子,五年前有专家预测这个职业将被算法横扫。结果五年过去,放射科医生数量不但没减少,还增加了。原因很简单:看片不是目的,诊断才是目的。AI 把任务做得更快之后,能诊断的病更多了,医生反而更忙了。如果你的工作只有任务,没有目的,那你可能危险了;但如果任务只是你实现目的的工具,那 AI 只会把你从机械劳动里解放出来,让你往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这个洞察其实比表面上深:AI 会消灭那些把“手段当目的”的岗位,逼着人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有点像你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切菜切得飞快,但其实餐厅挣的钱根本不是靠你切菜,而是靠菜做得好不好吃。AI 就是那个第一次把“你到底是厨师还是高速切菜机”的问题摆上桌面的人。
关于“AI 会不会产生意识”这种传统哲学式提问,黄仁勋不太喜欢。他的思路更贴近工程师:机器能否理解信息、理解指令、拆解任务、执行目标——他相信这是可能的;至于“意识”是什么,他没兴趣做形而上学的争论。他用的比喻很轻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人工智能”——也就是大脑;而大脑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限制的、不断自我校准的预测机器。换句话说,意识不是那种科幻式的神秘物质,而是一套模拟层叠上的涌现结构。人类都不是凭空产生奇怪念头的生物,机器也不会。
但他在 AI 安全的问题上倒是态度明确。他不是那种乐观到天真的人。英伟达自己内部的安全设计完全是“免疫系统模型”——每一层都假设可能出错,每一层都需要自检,每一层都要有边界。他不相信“大一统的安全神系统”,而相信让每个组件像细胞一样有自我意识,自我约束。他的逻辑很简单:你不可能预测一切风险,但你可以让系统学会自己纠偏。
访谈里最意外的部分,可能是他对能源的强调。普通人谈 AI,总觉得算力是关键;但在他那里,算力本质上只是能源转化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便宜且稳定的能源,就没有芯片工厂,没有 AI 集群,没有超级计算机。他对美国制造业的看法也完全围绕能源展开:如果没有能源增长,谈制造业回流只是空话;没有工业增长,谈就业也只是口号。他甚至直接说,未来十年的 AI 能耗对普通用户来说会“微乎其微”,不是因为 AI 省电,而是因为摩尔定律在另一条维度延续了:每一次迭代都把同样任务的能耗压低一个数量级。
某种程度上,他对美国制造业的乐观来自一种非常朴素的判断:国家安全一定会迫使关键技术本地化,而本地化一定会倒逼能源扩张。这个逻辑的推演听上去不如“AI改变世界”那么性感,但它可能是真实世界最硬核的那部分机理。
最具戏剧性的,是他对特朗普的评价。那些看新闻的人会觉得他一定持保留意见;但实际接触后,他完全不避讳自己的惊讶:特朗普比想象中更会听、更务实、也更直接。很多人对他的刻板印象来自电视,而不是现实。他讲了一个细节:特朗普几乎记住他和每个人说过的话,这在政治人物中并不常见。黄仁勋对他最大的认可来自一点——政策思维非常“常识化”,尤其是对制造业回归的执念。他甚至用“如果没有他的能源增长政策,我们根本建不成这些 AI 工厂”这种句式来表达一种完全出乎外界预期的肯定。
这些片段连在一起,呈现的是一个有点反直觉的黄仁勋。他不是神话里的“AI 狂人”,也不是舞台上那个不苟言笑的“技术领袖”,更不是华尔街想象的那种“只关心利润的算力销售”。他更像是一位从生死边走过多次的人,对世界的每一次变化都有着极度现实主义的敏感。他对 AI 的理解不是乌托邦式的赞颂,也不是世界末日式的警告,而是一种冷静的历史观:技术进步不是高潮式革命,而是长坡、厚雪;不是摧毁旧世界,而是修补旧世界的缝隙。
如果你非要从他的访谈里提炼一个核心,那大概是这句潜台词:未来不会突然到来,未来会一点一点逼近你。你如果不往前走,就会被拖着走。你如果走得够快,就能决定下一步是什么。AI 是洪流,但英伟达不是在等洪水来,而是在搭桥。而在桥底下,他每天仍然提醒自己:距离倒闭三十天。
这种荒诞又务实的心态,倒挺适合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