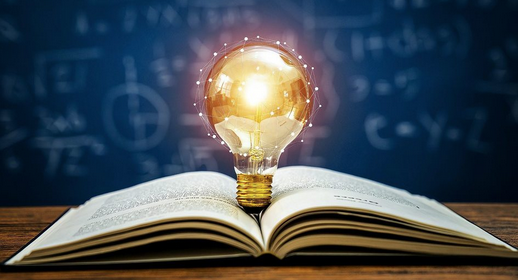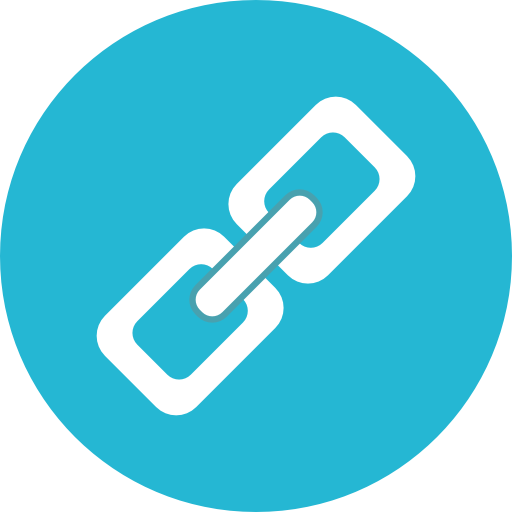达沃斯从来不只是一个会议地点,它是一整套全球秩序的“后台”。问题在于,在特朗普对纽森的侮辱性言论撕下了达沃斯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之后,这套后台正在崩塌,但塌得并不冤。
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1年由克罗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创立,标榜把“商业、政治、学术和社会其他领袖”聚在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好。
但半个世纪下来,真正始终缺席的,恰恰是“社会”本身——那些生活在国家里、在企业里、为这些“领袖”承担后果的普通人。达沃斯最擅长的,从来不是倾听,而是对阶层与身份的彼此确认。
先看门槛。成为 WEF 成员,每年要交6万到60万瑞士法郎(约6.2万至62.2万美元)的会费;每派一名代表参加达沃斯,还要再付约2.7万美元。
这不是公共讨论,这是付费俱乐部。学者、公益人士偶尔被“邀请”,不是因为他们重要,而是因为他们便宜、好用,能在大人物不关门密谈时,提供一点背景音——这不是文字的修辞,而是行规。
官方说,达沃斯不谈交易,只谈理念。但现实恰恰相反:当全球最有权力的一小撮人,被集中在同一座小镇、同一批酒店、同一段时间里,“不交易”反显得异常。
WEF 甚至自豪地列出“战绩”:1988年促成希腊与土耳其缓和关系;支持南非种族隔离的“和平转型”;推动政府与企业携手“绿色转型”。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没列出的“那些交易”。
1996年的俄罗斯“贷款换股份”计划,是达沃斯逻辑的经典样本:为了帮助叶利钦连任,西方金融体系向俄罗斯提供短期贷款,条件是允许一小撮关系密切的银行家控制石油、铝、镍和天然气等核心资源。
这场交易也许短暂“拯救”了俄罗斯的民主,但代价是制造了经济寡头,并最终为普京式的当选铺平道路。达沃斯也许不制造政治风暴,但它非常擅长为政治冲突提供温床。
民主,在达沃斯经常是输家。这并不奇怪,因为整个机制就是为绕开民主而设计的。
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求助国家施加了强硬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核心条件包括:在未考虑求助国家的具体国情的情况下,统一要求削减社会支出、劳动力市场“改革”、严厉紧缩。
这些政策未必写在达沃斯的会议文本里,但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观点的统一与利益对齐,并向弱国反复灌输一个信息:你们“别无选择”。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也是如此。它允许跨国公司因“预期利润受损”,在国家司法体系之外起诉主权国家。结果是,只要仲裁威胁存在,许多国内改革在落地前就被扼杀。钱没开口,民主已经噤声。
再看2008年金融危机。等各国财长和银行家2009年1月再聚达沃斯时,救助早已完成,系统已经“稳住”。而当时在达沃斯高谈阔论的的财长和金融家们,却没一个人真正想动手重构健康可持续的金融体系。
于是,真正的问题被留在原地:银行更大了,影子银行继续野蛮生长,系统性风险只是被重新包装。
至于达沃斯最爱自夸的“绿色转型”,结果更是讽刺。碳税因企业强烈反对而胎死腹中,取而代之的是碳抵消——不是因为它有效,而是因为它便宜,尤其便宜给那些最大的污染者。
从某种角度来讲,达沃斯确实定义了某些全球性的经济规则,但正因如此,它也必须为当下秩序的无序和断裂负责。
加拿大总理卡尼看得很清楚:这个旧秩序不值得哀悼。问题在于,如果“新秩序”仍然由旧秩序的设计者,在5000欧一晚的酒店与阿尔卑斯山稀薄的空气里构思,那结局不会更好,反而会更糟。
在《晋书·惠帝纪》中,晋惠帝司马衷和他的精英士大夫们,面对饥荒中百姓无粮可食的奏报,除了大臣们呱噪的争论,还有就是晋惠帝那句“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上层的精英们讨论得越久,战争和崩塌往往已经在山脚发生。当西装革领的财政大臣们还在空谈理论时,人道与经济危机早已爆发。
达沃斯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好想法”,而是它让错误的那群人,思考了太久、决定了太多。
如果随着就秩序的崩塌,达沃斯在未来的某一天宣布突然死亡,那它的退场并不值得人们同情与惋惜——当不该决定的人终于失去决定权,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好——至少不会比现在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