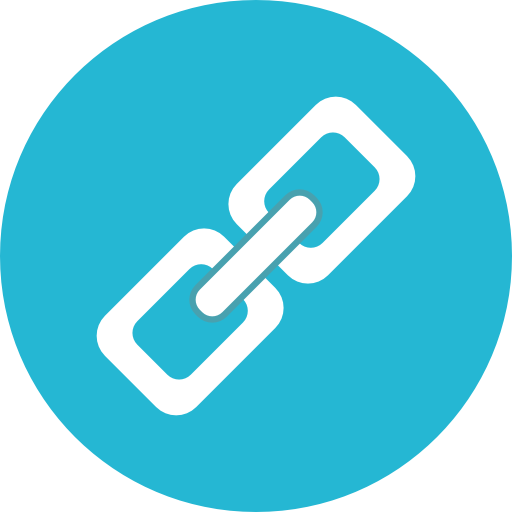二十世纪末的拉美,如果要选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国家,委内瑞拉一定榜上有名。
它拥有全球最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地理条件不差,人口规模适中,曾经是拉美中产阶层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委内瑞拉人均收入长期位居拉美前列,加拉加斯被称为“南美的迈阿密”,国民出国旅游像今天刷短视频一样自然。1999年雨果·查韦斯当选总统时,委内瑞拉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仍处在地区顶端,很少有人会把这个国家与“经济崩溃”联系在一起。
但二十年后,故事的画风彻底反转。委内瑞拉不再是资源富国,而成了现代经济史上最极端、最持久的崩溃样本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从2013年到2019年,委内瑞拉实际GDP缩水约65%,这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先例。通胀率在2018年一度达到百万级别,货币的功能被直接摧毁。工资不再是收入,而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医生、律师、工程师纷纷出走,难民人数在短短几年内接近五百万,规模直逼叙利亚内战制造的外逃潮,只是这里没有炮火,只有空货架。
有意思的是,委内瑞拉政府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相当“体面”的解决方案:停止发布GDP数据。官方统计口径仿佛按下了暂停键,但现实世界并不会配合演出。货币迅速贬值,现金比厕纸便宜并非修辞,而是市场给出的定价结果。
有人排队数小时,只为从ATM里取出一沓几乎没有购买力的纸张,用来证明“我今天努力过了”。这些细节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任何宏观图表都更刺眼的经济图景。
问题自然随之而来:一个资源禀赋如此优越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答案并不在某个单一政策,也不只是“领导人能力不足”这种安全但空洞的解释,而在于一整套在顺风期看起来正义、有效、甚至感人的经济叙事。
这套叙事的核心人物是查韦斯。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腐败寡头,也不是只为自己家族敛财的独裁者。恰恰相反,他对不平等有着近乎本能的愤怒,对底层贫困怀有真实而强烈的同情。他反复强调社会正义,痛斥既得利益集团,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切不公的源头。在一个贫富差距显著、传统政党信用破产的国家,这样的情绪极具号召力。
查韦斯提出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在理念上并不复杂。国家要掌控关键资源,尤其是石油;市场要服从社会目标;财富必须通过再分配流向穷人;政治权力要从精英手中夺回,交还给“人民”。听起来并不陌生,甚至让人感到熟悉和安心。更重要的是,在油价高企的年代,这套模式在短期内确实奏效了。
通过重组国有石油公司,政府将石油收入更直接地纳入财政体系,再通过一系列社会项目迅速分配出去。廉价食品、免费医疗、扫盲运动、土地再分配、社区委员会,这些政策真实地改善了大量底层民众的生活。贫困率一度下降,教育和医疗覆盖率上升,查韦斯的支持率长期居高不下。对很多委内瑞拉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觉国家站在自己这一边。
问题在于,这种“成功”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高油价。
1999年查韦斯上台时,国际油价在每桶20美元左右,随后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上行周期,在他去世前一度突破110美元。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掩盖了经济结构的脆弱,也让政策的真实成本被推迟结算。石油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提款机,唯一的问题是,大家开始把它当成了永久收入,而不是周期性红利。
在这个过程中,委内瑞拉逐渐走上了一条高风险的路径。财政支出高度依赖单一资源,社会项目缺乏可持续融资安排,公共部门不断膨胀。与此同时,大规模国有化和价格管制压缩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企业被征收,利润被视为不道德,价格被行政命令冻结,而成本却在真实世界里上涨。结果是投资消失,生产下降,供应链开始断裂。
到201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的私营企业数量相比1999年已大幅减少。农业和制造业长期萎缩,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反而更高。石油不仅没有成为工业化的跳板,反而成了结构单一化的催化剂。只要油价维持高位,这套体系还能勉强运转;一旦油价下行,脆弱性便集中暴露。
马杜罗上台后,油价的转向成为压垮体系的外部冲击。从百美元跌至四五十美元,对任何资源型国家都是挑战,但只有委内瑞拉跌成了“自由落体”。原因并不神秘:它几乎没有缓冲机制。没有主权财富基金,没有反周期财政规则,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收入下降时,支出却无法同步收缩,结果只能诉诸最原始的办法,印钞。
超级通胀由此启动,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货币发行不再是宏观调控工具,而是填补财政黑洞的唯一手段。当价格管制与货币泛滥同时存在,市场的反应只会更加极端:商品消失,黑市兴起,短缺成为常态。政府把这种结果归咎为“经济战争”,用军队进驻商店,用行政命令打击涨价,但这更像是对体温计发火,希望它不要显示发烧。
经济逻辑的崩塌,很快反噬了政治结构。因为这套模式本身高度依赖集中决策和敌我叙事,它天然排斥制衡机制。反对意见被视为既得利益的阴谋,市场信号被解释为资本破坏,独立机构成了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为了让经济蓝图“顺利实施”,权力需要不断集中,司法、议会、媒体逐步失去独立性。这不是偏离初衷,而是逻辑延伸。
当资源开始短缺,政治反而获得了一种扭曲的稳定性。救济物资由政府控制,分配本身就成了政治工具。对民众来说,“听话”不再是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唯一的生存策略。经济崩溃没有自动带来政权更替,反而加固了控制结构,这也是委内瑞拉案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回头看,委内瑞拉的悲剧并非源自某个反派人物的贪婪,而是一种在道德上极具吸引力的叙事。它告诉人们,复杂的经济问题可以用简单的正义感解决,不平等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消除,市场失灵可以用权力替代。当现实暂时配合时,这套叙事显得无比正确;当现实反击时,代价却由整个社会承担。
委内瑞拉曾经拥有一切避免悲剧的条件,却在繁荣中放弃了约束自己的绳索。希腊神话里,海妖的歌声并不邪恶,它只是太好听了。问题不在于歌声,而在于人类是否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对任何资源富国而言,委内瑞拉的故事都不是遥远的异国奇闻,而是一面镜子,提醒人们区分短期慷慨与长期理性之间,那条看不见却致命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