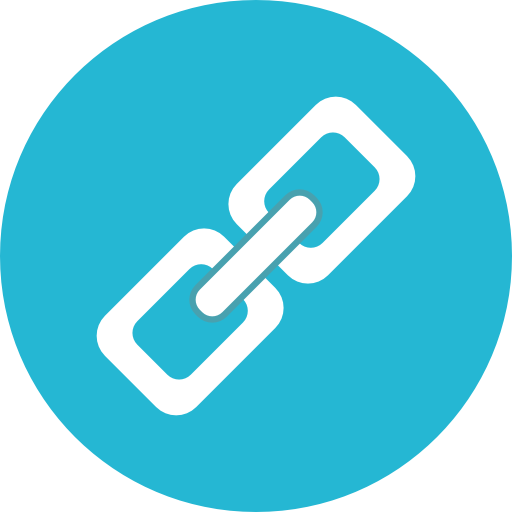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迎来了一位前所未有的掌舵者。12月17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30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亿万富豪企业家 Jared Isaacman 出任 NASA 局长。这不仅结束了此前由交通部长临时代理的过渡状态,也让这家全球最重要的航天机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交到了一个“非体制内”的人手中。
Isaacman 的简历放在任何一个政府任命名单里,都会显得有些离谱。他不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没有政党系统的履历,甚至连“长期公共部门经验”都欠奉。他更像是硅谷和华尔街合体后的产物:16岁高中辍学创业,靠支付业务做到公司上市,成为亿万富豪;业余时间学开喷气式飞机,飞着飞着顺手打破了环球飞行纪录;后来觉得地球有点小了,就自己掏钱上太空,而且一上就是两次。
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职业路径找一个关键词,大概只能是“兴趣驱动型资本主义”。
Isaacman 的第一桶金来自支付行业。16岁那年,他拿着祖父给的1万美元,在自家地下室成立了 United Bank Card,后来演变为今天的 Shift4 Payments。2020年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他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亿万富翁的跃迁。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并不是靠讲故事起家,而是标准的交易基础设施生意,现金流、客户规模、技术壁垒都相对扎实,这一点后来深刻影响了 Isaacman 看待航天的方式。
和许多富豪不同,他并没有在财富自由后转向慈善晚宴或艺术收藏,而是走向了飞行。Isaacman 拥有多种军用喷气机的飞行资质,累计飞行时间超过7000小时,还创办了运营全球最大私营退役战斗机机队的 Draken International。他对复杂系统、高风险环境和极限执行力的迷恋,显然不止停留在爱好层面。
真正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与 SpaceX 的深度合作。2021年,他自掏腰包并亲自担任指挥官,完成了 Inspiration4 任务,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完全由私人组成的载人轨道飞行。2024年的“北极星黎明”计划,他再次进入太空,并完成了私人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这两次任务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技术本身,它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载人航天,已经不再是国家机构的专属领地。
也正因为如此,Isaacman 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争议色彩。外界很自然地将他视为马斯克体系的一部分,一个由资本推上 NASA 顶层的“代理人”。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特朗普在胜选后最初提名 Isaacman,本就发生在他与马斯克关系最为紧密的阶段;而当两人关系一度恶化时,这项提名又曾被撤回,直到近期才重新推进并最终通过。
针对 Isaacman “马斯克代言人”的这一标签,他公开表示,自己与马斯克并非私人密友,合作 SpaceX 是基于当时的现实选择,而非私人关系。他甚至主动向蓝色起源示好,表示 NASA 未来应当同时拥抱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而不是绑定单一伙伴。从策略上看,这更像是一种主动去风险化的表态。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他和谁关系好,而是他打算如何重新定义 NASA 的角色。在听证会上,Isaacman 多次强调,国家航天机构不应再是一个“包揽一切的超级工程公司”,而应成为一个能够放大科学价值、整合私营效率的平台。他直言,未来的太空竞赛,胜负不取决于谁最保守,而取决于谁能同时调动国家资源和市场竞争。
这背后,是 NASA 现实而尖锐的压力。预算增长乏力,项目周期拉长,阿耳忒弥斯登月计划多次推迟,与中国在月球方向的时间表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已明确提出在2030年前建立可持续运作的月球基地,美国如果无法在这一窗口期内完成关键节点,很可能在下一阶段的深空竞争中失去主动权。
因此,Isaacman 上任后的第一个硬指标,几乎已经被写好:月球。
特朗普需要一个清晰、可交付、具备象征意义的登月进展;马斯克需要月球作为通往火星之前的关键跳板;而 Isaacman,则需要用一个足够硬的结果,证明资本并非只会侵蚀公共使命,也能提高执行效率。他在听证会上那句“如果有必要,我愿意自掏腰包推动项目上线”,听起来像是豪言壮语,但放在他的个人履历里,却并不显得突兀。
历史上,大多数 NASA 局长来自科学界或政府体系,擅长协调、审慎而克制。Isaacman 显然不是这一类型。他更像是一个习惯于在不确定中下注的人,一个愿意把个人声誉、资本和执行力同时押上赌桌的局长。
这当然带来风险。公共机构是否会被资本逻辑过度改造,国家资源是否会被商业目标牵引,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句“我和马斯克不太熟”而自动消失。但同样无法回避的是,在当下的地缘竞争和技术周期里,一个只求稳、不求快的 NASA,可能已经承担不起失败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Jared Isaacman 并不是 NASA 偏离传统的偶然,而更像是一种必然。宇宙仍然遥远,但NASA显然已经先一步,进入了一个更激进、更现实,也更不浪漫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