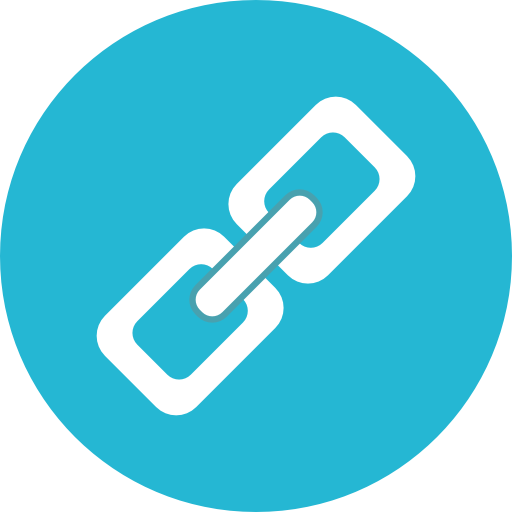永远要警惕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即便在“正常”的领导人治下,一个对自身地位高度焦虑的美国,也很可能会对外频频出手。
七十年前,处于衰落通道中的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并非典型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安东尼·艾登,是战后英国最具文化修养的首相之一。问题不在于领导人是否理性,而在于“地位焦虑”本身,足以让理性的人做出鲁莽的决定。法国陷入了一场在阿尔及利亚几乎注定失败的战争,英国则拒绝加入自己认为“没有前途”的欧洲联邦化进程——这些战略误判,至今仍在影响两国。
当然,美国今天的衰落程度,远不及当年英法那样陡峭。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是领先优势缩小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的衰落反而更难承受。英国当年还能安慰自己:权力正在移交给一个民主、英语文化、且在种族上高度相似的超级大国。而美国失去相对优势的对象,却是一个在制度、文化与价值观上都完全不同的国家。因此,尽管美国的相对下滑幅度小于当年的英国,但在心理层面,这种落差可能更具冲击性。你是“输给谁”,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再把特朗普那种对等级和排名近乎痴迷的性格因素加入方程式,一种像地质分层一样看待世界秩序的思维方式,就不难理解格陵兰问题上的粗暴姿态、加勒比地区的炮舰外交,以及其他类似“苏伊士时刻”的行动:它们本质上都是试图挽回失去的声望。
但即便换成一位“正常”的总统,美国此刻的行为可能也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对地位感到焦虑的国家,总会试图虚张声势。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超级大国能优雅地接受衰落。
如果你觉得问题只出在特朗普身上,那就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就已经开始对后来被称为“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感到不耐烦。即便不谈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轻蔑态度也十分明显。这并非对他的道德指控。过去和现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确实存在大量披着自由主义外衣、实则更偏左翼的虚伪表演。一个骨子里亲西方的总统,对此保持怀疑并非不合理。关键在于:美国对这种法律主义世界秩序的疏离,早于特朗普。这说明,困扰美国的并非个人风格,而是某种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可能正是相对衰落。
由于美国在本世纪的经济和科技成就过于耀眼,其相对衰落反而不容易被直观感知。但迹象确实存在:美国制裁的效果正在下降,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领先地位变得更吃力,军事差距,也早已不复千禧年初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一位普通的共和党总统,也很可能会采取对外强硬的姿态,只是未必像特朗普那样不加掩饰。
永远要警惕“向下流动”的力量。那些一生过得比出生时更好的人,很难真正理解地位下滑的心理创伤。哪怕绝对条件依然不错,只要社会地位稍有下降,就足以让人情绪失控。魏玛时期的德国,倒向纳粹的并非最贫困的人群,而是储蓄被通胀吞噬的中产阶级。在地缘政治中,这种心理机制只不过被放大到了国家尺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若不是对苏联解体后地位坠落的一种反抗,又是什么?
个人当然重要。但有些模式跨越时代、人物和地域反复出现。如果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衰落中的大国,能在接受新地位的过程中保持冷静与克制。特朗普的行为,是一种极端版本,但这种趋势本身,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很可能继续发生。
修昔底德那句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其命运”,最近被频繁引用,人们往往郑重其事地点头,仿佛它揭示了国际关系的终极真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这句话暗示,国家越强大,就越具有侵略性。可美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在1946年前后:它生产了全球一半的工业品,还垄断了核武器。但那个时代的美国,并没有肆意欺凌弱小,而是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这些堪称“开明利己主义”的杰作;它还重建了日本和德国,使其成为和平主义民主国家。美国真正变得更具攻击性,反而发生在其相对衰落之后。
领导力可以解释一部分差异,杜鲁门确实“好于”特朗普,但这不是全部。更关键的是结构性因素:当一个国家身处巅峰,更容易表现出宽容和克制;当位置开始下滑,偏执与攻击性便会随之而来。因此,在美国逐渐适应“众多超级大国之一”而非“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之前,我们有理由预期一个更加动荡的美国。英国和法国最终完成了这种心理与战略转变,尽管它们付出的代价更大。
人们总爱引用狄兰·托马斯诗中那句“不要温和地走入良夜”,却很少提及后半句,诗人最终承认,放下抗争或许更理性:“智者临终前明白,黑暗自有其道理。”
特朗普选择的是愤怒。但换作其他人站在他的位置,未必会有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