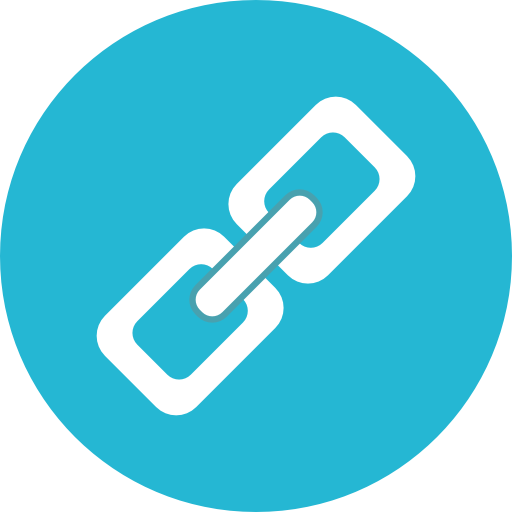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创造的,也不是家庭消费拉动的,而是由政府“刷卡”买出来的。
在一连串削弱增长动能的冲击之下,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国家正在放弃原本的节制路线,转而推出规模可观的财政刺激方案,用持续扩大的预算赤字托底经济。短期看,这种做法确实有效。摩根大通预计,受各国支出扩张推动,未来六个月全球经济增速有望加快至年化3%左右。
问题在于,这发生在一个并不“理想”的时间点:失业率处于低位,利率却仍处高位。经济学家的担忧也因此显得格外直白——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增长方式。
日本提供了最新注脚。首相高市早苗在提前大选前抛出增加支出、削减消费税的计划后,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迅速飙升至历史新高,债券抛售随即外溢至全球市场,美国国债收益率也被带着往上走。伦敦凯投宏观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形容,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暴露的是发达经济体长期被掩盖的脆弱性:私人部门需求疲软,生产率增长缓慢。
欧洲的处境尤为尴尬。在特朗普因格陵兰问题威胁升级贸易战的背景下,欧洲几乎找不到多少来自政府以外的增长引擎。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测算,今年美国和德国的财政刺激可能分别拉动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日本约0.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将连续第二年运行接近GDP 9%的广义财政赤字,这一规模大致是其预期经济增速的两倍。
各国政府如此“舍得花钱”,并非单纯为了对冲周期下行,更重要的是在为不断堆积的结构性难题买单:被人工智能重塑的产业,被关税和补贴挤压的出口企业,持续扩大的军费需求,昂贵的能源转型,以及快速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与医疗压力。
如果放在过去,这样的支出意味着一个简单直接的结果:加税。但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中,几乎没有多少领导人愿意把账单直接交到选民手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去年发达经济体平均财政赤字达到GDP的4.6%,新兴市场为6.3%,而十年前分别只有2.6%和4%。
在美国,今年约6%的GDP财政赤字,部分正是维持低税率政策的结果。高盛预计,随着关税带来的拖累减弱、减税效应显现,美国经济今年增速可能达到2.5%,高于去年的约2%。德国同样寄希望于万亿欧元规模的国防与基础设施支出提振增长,但现实是,德国的税负已处在发达国家高位,继续加税的空间并不大。
从全球范围看,德国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反而成了“异类”。IMF预计,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超过全球GDP的100%,创下1948年以来最高水平。
债市其实并非没有给过警告。2022年,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推出没有资金来源的减税方案,引发市场剧烈动荡,最终被迫下台;法国过去两年也因预算推进困难,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只是,与2010年欧债危机时期不同,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出逃。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里卡多·雷斯指出,疫情期间的经验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并不会立刻引爆危机。通胀虽然伤害消费者,却在短期内降低了债务的实际负担。这种“延迟成本”的特性,无形中强化了政府继续举债的信心。
更深层的变化,是政策取向的转向。金融危机后,紧缩一度被视为稳定市场的必要手段;而如今,各国逐渐接受一个现实:紧缩不仅政治上不受欢迎,还会换来军力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更脆弱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全球军费支出普遍抬升;加拿大批准未来五年约1400亿加元的新支出,用于升级港口和贸易基础设施;日本也推出规模相当于GDP 2.8%的刺激计划。甚至在欧洲,一些原本主张财政纪律的极右翼政党,也开始靠承诺“多花钱”来争取选票。
在美国,持续扩大的赤字既源于社会保障支出庞大,也来自长期压低税率的政策选择。前国会预算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温迪·埃德尔伯格认为,更多借贷确实会推高利率、拖累经济规模,但这些影响尚未大到不可承受。债券投资者普遍相信,美国拥有足够的财富支撑其债务,因此真正的“清算时刻”还很遥远。
然而,高通胀迫使央行加息的这一轮冲击,已经再次提醒市场:政府债务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失控。过去四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翻了一倍多,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偿债成本也大致翻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一旦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或者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长期经济收益重新评估,局面可能迅速逆转。
雷斯的评价更直接:他很担心,因为无论从任何历史尺度看,如今各国为债务支付的利息水平,都已经处在极高区间。
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举债维持运转。短期看,这套机制仍然奏效;长期看,却更像一种上瘾式增长——越借越难停,而代价,只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